理论研究|张景龙:《廖名缙佚文集》后记
经三年多焚膏继晷,夙夜不懈之劳作,到今天这部《廖名缙佚文集》(以下简称《佚文集》)总算完成了从搜集到整理,从校点到注解的全部工作。
对于这部《佚文集》,笔者原计划只做廖先生佚作的搜集,余下的整理、校点、注释等工作希望由作者故里县政府相关部门出面,聘请其他相关学者来做。因为笔者另有一个撰写廖先生传记的计划,希望能尽快实施。
廖先生系辛亥革命元老,近代湖南教育先驱,在清末民国初的军政文教界均遐迩著闻,亦有“光宣间知兵词人”之雅号,搜集整理出版他的文集对于湘西地方文化之挖掘与保护,尤其对于其故里浦市古镇先贤文化之打造更是意义重大,堪称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大好事,相信地方政府定会大力支持。
经过近两年之役役劳作,搜集工作于2017年9月基本告竣。当笔者将整个计划向泸溪县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汇报之后,该领导当即表态大力支持,同时嘱我尽快起草一个出版计划,争取于2018年下半年出版包括《佚文集》(上下)、《百槲溪堂文集》《楚南邵辰廖氏宗谱》以及《廖名缙传》等在内的整套文集。然而,当笔者把起草好的计划送交之后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揣测想是经费方面遇到了难题,因为做这样一套文集,包括聘请专家整理、校点、作注以及出版等所需费用毕竟不是一笔小的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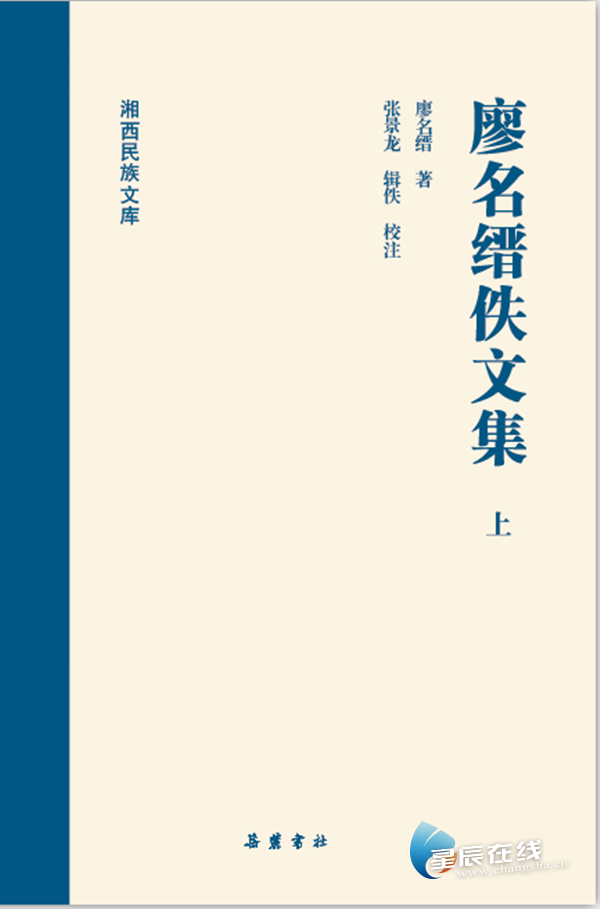 (《廖名缙佚文集》上)
(《廖名缙佚文集》上)
既如此,为了让这件功德之事能尽快完成,笔者只好把手头其他事情先搁置一边,亲自动手开始对所搜集到的廖先生佚作进行整理、校点、注释……又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劳作之后,一部共九卷的《佚文集》(上、下)初稿终于完成了。至此,我倒要感谢,感谢前一年的“入海泥牛”,是它让我意外地有了一次私淑作者廖先生的机会。通过校点研读注释他的作品,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他高洁的人品、广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情怀。
当然,在此过程中,很辛苦,但也常常收获着满满的成就感。除在前言中所述诸事之外,在整理、点校及注释过程中亦有不少有趣而难忘之事,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一二。
道是最易却最难
第一卷第一篇《入云山复修水星阁记》无须点句,因为该文最初录自雷公建喜所撰之《浦市》一书,而书中所载之文已经雷公整理点句,笔者只需抄录下来即可,由是最初感觉该文当是最容易的一篇。不料读至其中“经主持僧照升,不远千里赍父老热忱毅力”一句时,却怎么也读不下去了。“赍”是“持,携带”之意,何以“不远千里赍父老热忱毅力”?此乃何意?
再三琢磨,总感觉此句有问题,然手中既无其他版本,因无从校勘。但发现文后附有“此文原载于《泸溪县志》1929年版”,于是尝试找寻这部县志,以查看最原始版本。但县志没找到,却找到了泸溪县政协文史委编印的泸溪文史第八辑《浦市镇》一书,该书中亦收录了是文。可当仔细阅读之后发现,该书所录之文除出现一些诸如“蟠阻”误为“蟋阻”、“坑冶”误为“坑治”等谬误外,最关键的那一句仍与雷公建喜的《浦市》一书无异。
笔者性格中有一特质,褒者称之“执着”,贬者谓之“固执”。虽然两书中这一句俱无差别,然笔者仍执念此句定有问题,于是继续寻找县志。一段时间后,虽然1929年版县志仍未找到,却找到了1993年版《泸溪县志》。令笔者兴奋的是,该县志在459页上亦收录了此文。而且在文中找到了笔者苦苦搜求的正确答案:原来前两书中果然有误!原文是“经主持僧照升不远千里赍父老书来咨度。余亟赞许,以道艰不克一返里门,勷兹美举。赖诸父老热忱毅力,未久遂告成功。”前两书中在“赍”与“父老热忱毅力”之间漏阙了“父老书来咨度余亟赞许以道艰不克一返里门勷兹美举赖诸”如此长的一节内容。而将这一节补正后,文意便非常清楚且文句亦十分通顺了。
既又寻到一个版本,照例再进行一次认真的校勘。不料在校勘过程中又发现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标题。前两书中的标题是“复修入云山‘水星阁’序碑记”,而1993年版县志中的标题乃“入云山复修水星阁记”;二是作者于文中述及其先人时之敬称不一致。文中共有两处对其先人的敬称。前一处在两书中均为“先大父鼎五公”,而在县志中却是“先父鼎五公”。另有一个敬称“先父”则三个版本无异。“先大父”是晚辈对已故祖父的敬称,“先父”则是对已故父亲的敬称。三个版本两个不同的敬称让同一个人竟然成了两代人!一为作者之祖,一为作者之父!那么孰是孰非?作者所述之人究竟是谁?乃父?抑或乃祖?
好在称呼后有“鼎五公”字号,这对笔者来说就比较容易考证,因为早在2016年下半年笔者就从美国犹他州家谱协会图书馆设法弄到了作者亲自编撰的《楚南邵辰廖氏宗谱》(以下简称《廖氏宗谱》)。据《廖氏宗谱》记载,作者之父名廖华菁,字竹亭,一字莪士;而作者之祖名为廖荣禄,字鼎五。由是文中所述之人便可确认县志上的“先父”乃谬误,而前两书中的“先大父”为正解——因为“鼎五公”乃作者之祖。
第二个问题解决后,还有第一个问题,即文章之标题孰正孰误?非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1929年版的泸溪县志,查看最原始的版本。可此前为搜寻该县志已经耗费过不少时间未果,若再为此事耗时就会耽误整体进度。好在两标题并无太多意义上之谬误,只涉及文字上之细微差异,因而暂以最初标题为准,考证之事留待以后再说。
2018年下半年,《佚文集》初稿刚完成不久,一天,中山大学的一个陈姓博士来笔者的创作室咨询有关浦市的一些情况,无意中得知她手中竟然有1929年版的县志!原来1929年版的县志名并非叫《泸溪县志》,其全称叫《泸溪续修县志》。这可真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语!通过查考最原始的版本,发现该文标题与1993年版县志上的一致,于是最终采用了县志上的标题。
但是,在根据《泸溪续修县志》再次对该文校勘的过程中,笔者又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前两书中之“先大父”,在1929年版县志上却是“王父”。“王父”跟“大父”一样,均系晚辈对祖父之敬称。那作者原文中究竟是“大父”还是“王父”?当然这其实已非太大问题,但为准确起见,笔者再次查阅了《廖氏宗谱》,发现作者在多篇文章中都述及其祖,且其敬称均为“先王父”,仅在撰写其四位从祖传略时使用过一次“大父辈”。由是这个问题自然以1929年版县志为准。
第二个问题是,在另一个敬称上又出现了辈分不一之情况。前三个版本中均是“先父”,而1929年版县志上却仍是“先王父”。1929年版县志所载之文系最初版本,按说以此为准当无不妥。但笔者仍不放心,因为笔者从该县志的序言中得知,这部《泸溪续修县志》并非民国刊本,而系整理者根据“文革”时期从准备焚烧的废纸堆中偷偷保留下来的油印本整理,于2008年才重印的,而且据整理者在志序中介绍,且从所附图片亦可看出,当初的油印本字迹相当模糊。作者之父祖两代均系贡生,父是拔贡,祖是岁贡,那么文中所述作者儿时追随其至入云山寺馆“讲学”者究竟系其父抑或其祖?
这个问题若是在最初发现时要弄清还真是个大难题,因为作者虽在宗谱中撰有其父、祖之传略,但均未述及这个问题。好在笔者的初稿已经完成,印象中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有述及过。于是在全书所有文章中查寻,很快在“轶闻琐录”卷中一篇题为《张国玉先生》的短文中查到“余祖馆入云寺时,每过其肆,必中途小憩,与谈乡曲琐事。”由是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泸溪续修县志》中之“先王父”当是正解!
第三个问题是“康、唐”之辨。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当年的两位学友。其中第二位学友的姓氏在前“二书一志”中均是“康君渠仙”,而在《泸溪续修县志》中则为“唐君渠仙”。但此时已无其他版本可考。按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应以后者为准,因为1929年版《泸溪续修县志》毕竟是刊载本文之最初媒介。然思忖再三,笔者最终仍采用前三文中之“康君渠仙”。理由有二:一是因为笔者所见到的《泸溪续修县志》并非1929年的原始刊本,而是根据字迹不清的油印本整理于2008年重印而成。既字迹不清,而“康、唐”二字又外形相近,因此整理时极易出错;二是因为《浦市》一书的编撰者雷公建喜于1922年8月出生,作者去世时他已有5岁,且生于斯长于斯,其少时当见过至少听闻过康公其人,亦应见过水星阁的碑文。因此仅就文中所述之人名而言,雷公建喜当不会出错。
一字之变意迥然
在注解作者那首著名的《自度曲》时,遇到了一个十分罕见之情况,由于这个情况的出现,导致笔者对后半阙的注解思路作了很大的改变。
该《自度曲》最初录自清末民初京津文坛领袖郭则沄所编撰的《清词玉屑》。下半阕有一句“梦里琼波,匣中锦字。”最后一句是“曼殊要看秋发”,这两句中竟然涉及两位佛教人物。
第一位“琼波”,即琼波南交,全名为克珠·琼波南交,系香巴噶举派创始人,出生于尼木热芒地区琼波氏家族,“琼波”为其家族姓氏。第二位“曼殊”,即曼殊室利,即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文殊菩萨。除下半阕中的两位佛教人物外,上半阕中亦有“正佛火蒲团”句。而作者晚年奉佛,不仅常在大型佛教活动中为信徒们宣讲佛学,且曾任过九世班禅活佛的秘书长,由是自然让人想到该词或与佛教相关。
据克珠群佩主编的《西藏佛教史》介绍,琼波南交前往索萨林洲,拜谒那若巴的明妃妮谷玛,获得《幻身》和《梦境》灌顶,在梦境和真实中获得了金刚持明妃所传《妮谷六法》《金刚偈句》《幻身道次第》等。如果将句中之“锦字”不作“锦字书”而作“华美的文辞”解,那“梦里琼波,匣中锦字”之意境岂不与琼波南交的故事十分契合?
然当笔者按此思路将这几句注解完之后,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作者乃情感非常丰富之人,对以词寄情之作极为赞赏。譬则他在评价尚镕《咏小孤山》时就曾写道:“往来词人题咏甚夥。而写景者多,寄情者少。惟尚镕一绝,情景兼到,当为此题绝唱。”然是首《自度曲》读到下半阕时,感觉从“梦里琼波”始,该词前面所寄之孤忧哀愁似乎到此戛然而止,突然把读者思绪引入了佛之意境。
一天,笔者无意中发现了作者另一首诗《奉题<湘楼听雨图>》之线索。当笔者沿其线索溯至该诗出处——徐珂的《康居笔记汇函》时,竟然发现其中除了这首诗作外,徐珂还记载了《自度曲》及其由来。原来这首《自度曲》系作者专为徐珂之《纯飞馆填词图》所题。仔细校勘之后发现,该词中除有几处点句与《清词玉屑》中存在差异外,竟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迥然不同:《清词玉屑》中的“梦里琼波”,在徐珂的《康居笔记汇函》中竟然是“梦里湘波”。一字之差,意思却相去万里。果真是“湘波”,那注解的思路就要完全改变!
然笔者手中的《康居笔记汇函》系山西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7月所出,而据介绍徐珂的《康居笔记汇函》最初版系1933年刊本。那会不会是山西古籍社的版本有误?于是笔者又想法从某古籍书商手中购到了该书的民国刊本。经校勘之后发现,山西古籍出版社的版本没错,民国刊本中亦是“梦里湘波”!由于作者该词最初是专为徐珂所题,一切理当以他所记载的为准。于是笔者断然废掉了原来的注释,重新作注。
一字之变,下半阕整个意思就完全顺畅了。原来作者词中的“湘波”指的是“湘江之波”。既是“梦里”湘波,那该首词当系作者离湘赴京之后所作。作者在长沙生活过多年,夫人去世后的第二年才正式定居北京。结合前一句“只有双鬟难觅”,不难看出,作者在整首词中所流露出的孤忧和哀思均与其早逝的年轻妻子相关。
作者四十一岁时娶了年仅十九岁的第二任妻子邓继梅。而邓氏女又是作者任浏阳教谕时的好友、该县县尉邓蔚楼先生之女,作者在浏阳初次见到邓女时她才九岁,十年后嫁给作者,一九二○年病逝时年仅三十一岁,而作者彼时已逾知命之年,当时心中的那一份伤痛可想而知。二人虽是夫妻,但妻子小他二十二岁,因而在他的哀思中,妻子永远是当年的“双鬟”少女。而他对夫人之所有回忆均与长沙相关,是以以“湘波”借指长沙,进而暗喻亡妻。而且自一九一五年夏始,作者先是任职北京,继而任职常德,再往后是重庆、成都、天津等地,与家人聚少离多,因而“匣中锦字”当指作者珍藏的夫人生前写给他的书信。
因此,一个“湘”字之更,让读者在读到后面“回首春灯,历历归去也”一句时,已然愁肠百结,唏嘘不已!自然对最后一句“还愁室里,曼殊要看秋发”也很好理解,深为认可了!
瘦身删字十六万
初稿告竣之后不久,具体负责《湘西民族文库》的湖南省湘西州政协委员会学习联络委副主任向海军先生让我把初稿先发过去,因为出版社要报出版计划。
2018年底,海军先生向我转达了出版社编辑的意见,除表达了对该佚文集的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外,同时希望笔者能将该文集中的注释内容压缩精炼一下。笔者前年着手注解时,一来编委会对各注释有引证之要求,更重要的是,笔者觉得廖先生的这套文集出版后应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普通读者借助注释能较为流畅地进行阅读。这样便可让更多的人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深邃思想和渊博学识。基于这样一种思路,笔者在注释时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工具书及相关史料文献,由是注释部分自然比较详细。
而既然出版部门希望将注释部分进行精炼压缩,笔者虽心中不舍,却也只好狠下心来定下三条较为严格的“瘦身”原则:一、除个别特殊例证外,所有引证之句全部删除;二、除个别极生僻文言字词外,凡词语之出处全部删除;三、大概能猜出意思的字词注释原则上亦删除。
诚然,当耗费大量心血所做的注解被一条条删掉,当全书的字数成千上万地减少时,心中不时会感到隐隐作痛。但尽管如此,笔者仍严格按上述既定三原则,一路砍伐削剪。其中最为“猛烈”的是把从《百槲溪堂文集》中选录过来的数篇赋铭赞作及其所有注释全部删除。
笔者当初之所以从《百槲溪堂文集》中把这些作品选入本《佚文集》中,旨在让读者能更全面欣赏到作者各类韵文体作品。而之所以现在要把这些作品连文带注释一起删掉,是因为出版社及编委会拟将《百槲溪堂文集》亦纳入出版计划。删掉这些作品,是为了避免在同一出版社的读物中出现重复内容。
随着这些作品的删去,原来的“歌赋铭赞”一卷中的作品所剩无多,难以单独成卷,故将余篇并入其他相关卷中。由是《佚文集》由原来的九卷便缩减为八卷,原“歌赋铭赞”卷不复存在。
当整个“瘦身”工程全部完成之后,这部《佚文集》总计被删掉了十六万字!仅诗词卷的注释就删去了十万零七百字!
长揖致谢待衔环
《佚文集》(上下)全书整个工程至此终于全部告竣。在此书从辑佚到出版的各个进程中,除笔者在《前言》中言及且鸣谢过的人之外,笔者在此还想感谢一些人,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佚文集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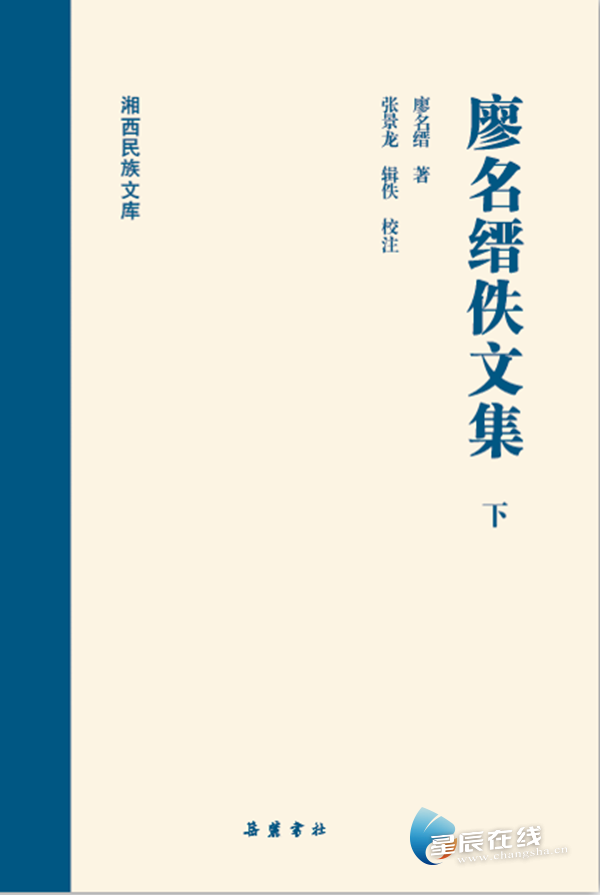 (《廖名缙佚文集》下)
(《廖名缙佚文集》下)
我要再次感谢该书作者之后人,如其季女、今已九八高龄的廖盛慈(太素)先生,除把珍藏多年乃父的《国风集评》手稿提供给笔者外,亦不顾耄耋高龄为该书撰写弁言;还有作者之嫡孙女、广东肇庆学院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廖萱女士及其丈夫李如喜教授,他们从头至尾全程予以关注、关心并以各种方式提供支持和帮助,常常令笔者有一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温暖和感动;作者之外孙女、重庆市万州区调研员田奉婴女士亦对是书提供了积极热情的帮助。
湘西州政协主席刘昌刚先生对该《佚文集》所给予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以及时任州政协学习联络委副主任向海军先生对该书所倾注的大量心血,都为该文集的出版面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吉首大学前党委书记游俊教授,吉首大学前正校级督导、著名学者张建永教授,吉首大学武陵山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登巧教授,著名古籍考证专家吕华明教授等对该《佚文集》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泸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尚远道先生,县民宗文旅局局长李玉梅女士等亦对该文集的辑佚工作给予过高度关注和支持。
在此,笔者对上述各位领导和朋友以及诸多未提及姓名而对该文集给予过关注、关心和帮助的朋友兄弟致以衷心的感谢!相信作者笏堂公在天之灵亦然同谢矣!
虽然《佚文集》的辑佚工作至此已全部完成,但毕竟是第一次校点笺注一位有“光宣间知兵词人”之誉、当年船山学社哲学主讲的儒学大师作品,因此存在谬误实属难免,还望各位方家读者不吝指正,笔者在此先行长揖谢过!
最后,笔者以一首小诗来结束此跋文,该小诗实乃《前言》各节之标题,亦是这部《佚文集》之全部写照:
斓斑碎玉弥足珍,秉文兼武赤子情。
鹤鸣在阴待子和,痀偻成蜩八卷经。
(《廖名缙佚文集》将于近期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发行)
【来源:星辰在线】

